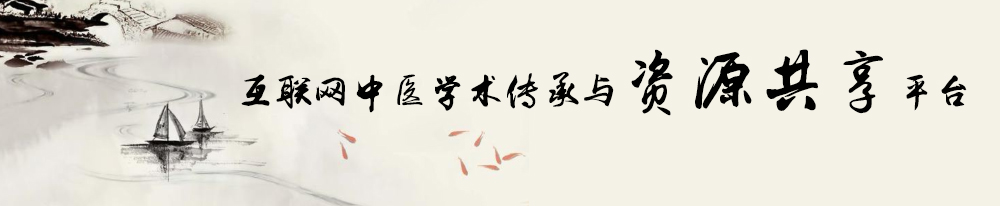杨建宇 北京知医堂门诊
摘要:中和医派是传统中医学的精华,近年来,中和医学的临床作用及地位也越来越高,杨建宇教授作为中和医派的代表人,其思想和理论在多个疾病领域中发挥着重要指导意义。对于免疫疾病的诊疗,中和医派杨建宇教授经方可在临床中开拓治疗思路。
关键词:中和医派; 杨建宇; 免疫疾病; 中医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Yang Jianyu in treating immune diseases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Yang Jianyu Outpatient Clinic of Beijing Zhiyitang
Abstract: The Chinese Medicine School is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recent years, the clinical role and status of Zhonghe Medicine are also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Professor Yang Jianyu,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is thoughts and theories play an important guiding role in many disease fields.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immunological diseases, Chinese Medicine sent Professor Yang Jianyu to develop treatment ideas in the clinic.
Keywords: Chinese Medicine School; Yang Jianyu; Immune disease; Chinese Medicine
中和思想作为儒家的核心思想,强调天地万物处于平衡状态,达到万物存在和发展的最高境界,中和思想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已确立了其正统地位,同时中和思想也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哲学基础[1]。中医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和思想已深深融入中医防治疾病的过程中,它无处不在,无声无息,深深影响着中医的思维和哲学体系,中医离不开中和思想,中和思想促进中医不断进步[2]。杨建宇教授作为学验俱丰的中医临床专家,临床经验以调和气血为本,谨守中和之道,善用经方为法,不忘攻邪之术,以中医药防治免疫性疾病为临床学术专长[3]。现结合中和医派杨建宇教授经方治疗免疫疾病的经验点滴略述如下。
1 中和医派要义
中和思想的“中”定义为“不偏之谓中”,反映了“中”为“正”,即不左不右,不上不下,恰到好处,无过而无不及。“中”是一种手段,讲究适中之意,强调人不管在何时何地,都要根据实事,掌握随机应变,同时中和思想的“中”还涵盖了循道的思想,要求不管在治国、处事,还是行医中,都应遵循事物合理的制度和规律,寻求原因,对症下药[4]。“和”的内涵是指和谐,在自然界中,人与他人、与社会,以及与自然环境之间都存在一种无形的关系网,在这关系网中,和谐不仅作为万物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事物存在的本质,只有处于和谐中的事物才能长久生存和发展。而“中”与“和”之间的关系即“和”是中的标准和结合,通过“中”实现“和”。
中医学认为,人体机能出现各种不同程度的病证,原因在于阴阳失调,阴与阳是人体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一对矛盾体,阴阳相互制约、相互转化,在不断的消长和平衡中,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5]。当人体阴阳无法保持平衡状态,阴阳相互制约转化的规律被破坏,人体的中和状态就会被打破,因此成为病理变化的决定因素。
中医学防治理论的根本目的即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保持机体平衡状态免遭破坏,或通过调节气血阴阳、脏腑功能的失常,使机体恢复平衡状态[6]。杨建宇教授总结中和医派的临床三要点:一要善于调气血,二要善于平升降,三要善于衡出入,并将慈悲为本、仁爱为先、一视同仁、中和乃根作为临床基本原则[7]。中医治病,当先审证求因,明确病机,然后确定治则治法,再遣方选药。
2 西医学对免疫疾病的认识
免疫疾病包括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继发性免疫性疾病,一般情况下提到的免疫疾病指的是自身免疫性疾病[8]。目前已知多种途径可引发自身免疫,免疫系统作为日常监视人体状况的系统,当机体出现感染、发生肿瘤等,免疫系统就会启动免疫反应,清除各类病原体或病变细胞,若因遗传等因素的作用下,免疫系统会发生过度激活,可能会错误攻击自身正常的组织和细胞,引发组织、器官损伤,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生。通过作用于多个效应器,免疫系统能引发自身免疫病,且大多数发病机制均通过活化自身反应性辅助性T细胞来完成[9]。辅助性T细胞按照其分泌的细胞因子类型可分为Th1和Th2亚群,Th1可促进细胞免疫生成,Th2以产生白细胞-5、白细胞-4、白细胞-10等为特征,主要作用于通过促进抗体生成,发挥对细胞外的入侵物的防御作用,同时Th2造成的破坏效果较小[10]。西医进行治疗免疫疾病以控制发病诱因,并抑制或阻断体内病理性自身免疫应答为原则,针对具体疾病类型,给予激素类、非甾体类、免疫抑制类等药物和手术治疗,但西药的作用机制较为单一,常出现反复发作和慢性迁延的趋势,病情较难控制[11]。
3 中和医派对免疫疾病的认知要点
中医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的《黄帝内经》就有记载关于人免疫相关的论述,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医学派和学家探索,在明代医书《免疫类方》中,首次出现“免疫疫疠”一词,“免疫”在当时被寓意身体抵抗侵害、恶劣的外在环境的意思。随着中和思想的传播,中医学越来越讲究天人合一,诊治要求从整体角度出发,结合患者症状证型和体质,并以整体调节、平衡阴阳作为基本原则[12]。
肺主气、合皮毛、主卫表,机体抵御外邪内侵的第一道防线就是由肺和卫气构成,病菌易从鼻腔吸入进气道,肺是病菌侵入的第一个部位,肺主宣发肃降,通条水道,肺的功能中和医派的观点认为其类似于非特异性免疫作用[13]。脾主运化,是水谷生化之源,开窍于口,在体合筋,主要决定着食物中的营养吸收和能量转化,脾与免疫功能关系密切,健脾可提高免疫功能。肾藏精,主生长发育与生殖,中医将肾评价为“肾者,精神之舍,性命之根”,若肾失去了动态平衡,会发生阴阳偏盛偏衰,肾的阴阳两个方面在人体内部既相互对立,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相互滋生[14]。
4 中和医派杨建宇教授诊疗免疫疾病的经验点滴
4.1 重视气血
中和医派的观点认为,气是构成人体的最基本的物质,“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气聚则形成,气散则形亡”。中医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气能够维持人体生命活动,卫气属正气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免疫防御功能,病邪侵入机体后,正气奋起抗邪[15]。在经脉运行之外,分布着不受脉管约束、遍及全身的卫气,卫气具有抗御外邪入侵、护卫肌表的作用。卫气的功能与西医理论中体液中的非特异性杀菌物质、吞噬细胞的吞噬作用等天然防御系统的作用相似。
中医将自身免疫性疾病归属“虚证”范畴,患者多以气虚、气短为症状,以气血两虚、气阴两虚为多见证型,病因与“禀赋不足,正气虚损”、“后天失养,五脏不坚”等有关,因此调理免疫疾病重在调理气血。杨教授治疗免疫疾病时,秉持临床思辨特点,即调气血、平升降、衡出入、达中和,强调纠正阴阳气血之偏盛,调理发病病机之失偏,适时引用当归(补血活血养血)、黄芪(补气升阳、利水消肿)、丹参(祛瘀止痛),并施以四君子汤、四物汤,遣四君四物,平气血阴阳偏盛,抓住根本,三帖可效[16]。
因此,当机体气血充盈,气机调畅,正气充足,在稳定体内经络、气血通畅的同时,提高抗御病侵、抑制疾病发生[17]。
4.2 重视调肺、脾、肾
机体抵御病侵功能的强弱与肺输布卫气能力的强弱存在一定关联,经脾胃运化食物的精气与肺吸入的清气相结合,即形成肺气,只有肺气宣发输布正常,卫气才能发挥其功能。西医认为,肺可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免疫系统功能,肺不仅作为呼吸气体交换的场所,同时也是抵御外来刺激和侵染的防线,在肺部的溶菌酶和巨噬细胞不断地在清除细菌和病原,呼吸道的纤毛运动也在将入侵的异物排出体外。同样在中医的观点里,肺气向上升宣向下通降,保持肺部和呼吸道的洁净,若肺气失宣,则卫气失职不固,开阖失常,邪不可干,外邪将乘虚而入,其气必虚,抗病能力低下[18]。
脾统血,汉代名医张仲景有“四季脾旺不受邪”的说法,实阐述了“脾”与免疫系统的关系,中医中的“脾胃”不仅包括消化系统,同时将淋巴器官、造血器官和外分泌腺归于其中。同时,脾为后天之本,脾气健运,水谷精微充足则卫气强盛,机体抗病力强,脾胃虚弱,脾气缺乏,运化无力。杨建宇教授针对脾虚证患者施以四君子汤能明显提高减退的免疫功能,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四君子汤中的人参有效成分为人参皂苷,可通过促进特异性免疫淋巴细胞的分化、增殖,进而提高嗜中性细胞和非特异性免疫NK细胞活性和吞噬能力,改善免疫功能,此外白术中的白术多糖还可通过改善消化功能,增加免疫球蛋白的产生[19]。
肾气由肾精产生,肾主骨生髓,中医对于免疫虚弱型疾病,一般将“补脾肾以故其本”作为基本原则,只有肾阳的温煦供给脾阳,二者才能更好地运化和发挥其功能。现代细胞发生学的角度也表示,骨髓作为免疫活动细胞的主要来源,因此肾决定这免疫功能。肾虚使人衰老,使免疫细胞减少,因此临床上抗衰老的中药中,绝大多数有补肾的功效[20]。
4.3 重视扶正祛邪
临床常用的扶正祛邪法分为补脾益肺法、活血祛瘀法、补肾法、清热解毒法、补阴法,多选用温补肾阳、补阴、补齐、补血、清热解毒等药物。健康是因“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而发病是因“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扶正祛邪作为中医治疗免疫性疾病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时期均是由于正邪相争,强调邪气致病,而且在机体既病之后,正气的盛衰也起着决定性作用,邪胜正则病进,正胜邪则病愈,因此治疗不外乎改变正邪力量对比,扶助正气,驱除邪气。
4.3.1 免疫兴奋剂
免疫兴奋剂以补益药物为多,现代药理学研究表示,白花蛇舌草(清热解毒)、黄芪(补气升阳)、刺五加(补中益精)、白术(健脾益气)、黄连(清热燥湿)、灵芝(护肝解毒)、人参(补气固脱)、黄岑(止血泻火)、当归(养血活血)、党参(健脾和胃)等能提高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红花(散湿去肿)、女贞子(补益肝肾)、王不留行(活血通经)、地黄(益气清火)、天冬(养阴润燥)等可促进淋巴细胞转化。
4.3.2 免疫抑制剂
丹参(化瘀止痛)、生甘草(祛痰止咳)、板蓝根(凉血利咽)、大枣(保肝护脾)、桃仁(润肠通便)、苍术(祛风除湿)、茵陈(疏利肝胆)、连翘(散结消痈)、大黄(泻火解毒)等有抑制抗体生成的作用,蝉蜕(宣散风热)、乌梅(止咳化痰)、苦参(清热利湿)等由抗过敏的作用,柴胡(疏肝解郁)、灵芝(护肝解毒)、仙灵脾(补肾壮阳)、牛膝(化瘀通经)、白蒺藜(祛风明目)、防风(解表止泻)等有抑制过敏介质释放的作用。
4.3.3 免疫调节剂
使用具有双向免疫调节作用的生脉散(益气生津)、玉屏风散(固表止汗)、穿心莲(凉血消肿)、青蒿(益气通便)等药物,使免疫反应偏高者向低调节。一般西药缺少双向调节的作用。杨建宇教授通过吸收张氏攻邪方法的精髓后,运用白茅根,利小便、祛心火,且性味平和,属于祛邪不伤正之佳品。
扶正、祛邪是一对矛盾,通过扶正可提高低下的免疫功能,而“邪去”后“正复”,带来了免疫力的提高,这对矛盾又符合中和医派治疗的辩证施治原则,“补之得法,祛邪对症”才能“调节阴阳、以期为平”,改善免疫功能。
5 经方要义
中和组方的基本原则为:1.遵经方之旨,不泥经方用药,2.谨守病机,以平为期,3.中病即止,不滥伐无过,4.从顺其宜,病人乐于接受。中和组方要领包括:一忌在未固护正气的前提下施以大热大寒大补大泻之剂;二忌过度滋腻,过度攻伐;三忌崇贵尚奇,以昂贵难求、不可寻求之奇药怪药而求奇验[21]。
中和组方用药强调谨守病机、以平为期,方药中要升降相应、阴阳结合、寒热共享、收散兼容、动静结合等。以期在保证用药安全的前提下,达到药到病除的目的。杨建宇教授“三联用药”的思路在于,按照君臣佐使模式组方用药,需充分发挥其相须、相使、相畏、相杀的功效,例如西洋参、生黄芪、紫丹参组合,可益气活血,每组功效可明确扶正组合、攻邪组合和辅助组合。杨建宇扶正祛邪中和汤的基本方包括:君:生晒参、生北芪、紫丹参,臣:北柴胡、川郁金、制香附,佐:法半夏、广陈皮、淡黄岑,使:大红枣、生姜片、生甘草[22]。
综上,杨建宇教授对经方有独特的理解和运用,在临床的实践中拓宽了思路,对于经方的传承和发扬也做了极有价值的推广,也使得中和医派在免疫疾病治疗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谭烨, 田永衍, 任红艳. 先秦"中和"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J]. 西部中医药, 2016, 29(13): 53-55.
[2] 罗桂青, 李磊. 浅析传统中医理论中的中和之道[J]. 中医学, 2016, 5(4): 137-140.
[3] 穆俊平, 魏素丽, 严雪梅, 等. 中和医派杨建宇教授临床诊疗糖尿病学验点滴[J]. 光明中医, 2017, 32(14): 2025-2027.
[4] 刘应科, 孙光荣. 以中和思想组方用药——遵循经方之旨,不泥经方用药[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5, 35(9): 1011-1018.
[5] 邓成海, 刘佩. 浅析中医阴阳理论与壮医"阴阳为本""三气同步""三道两路"理论的异同[J]. 中国民间疗法, 2020, 28(5): 17-18.
[6] 杜宏波, 李悦, 杨先照, 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中医药疫病预防与治疗的思考与展望[J]. 中医杂志, 2020, 15(18): 1052-1059.
[7] 宋欣阳, 陈丽云, 严世芸. 中和正义——探中和思想内涵与中医学[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5, 16(5): 1593-1596.
[8] Ep A , Mr B , Fl B .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with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filtration versus CLL-associated auto-immune disease with neurological involvement: A tricky differential diagnosis - ScienceDirect[J]. Revue Neurologique, 2020, 176(12): 120-123.
[9] 杨琴, 张改连, 高晋芳, 等. 间充质干细胞及其来源的细胞外囊泡在自身免疫病B细胞中的研究进展[J]. 中华风湿病学杂志, 2020, 24(5): 338-341.
[10] 杜恒, 高全彩, 苏振丽, 等. 二仙消瘿汤对桥本甲状腺炎患者免疫性抗体,Th1/Th2相关细胞因子的影响[J]. 中医学报, 2020, 35(12): 203-207.
[11] 张志斌, 郭仁德, 孟珂伟, 等. 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在围手术期中应用糖皮质激素的体会[J]. 中华普通外科杂志, 2020, 35(11): 896-897.
[12] 孙淑君, 张彦丽, 孙锋, 等. 清热消癜方治疗初诊断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疗效及对IL-10、TGF-β1影响的研究[J]. 四川中医, 2019, 37(2): 72-75.
[13] 李德帅, 王芙蓉, 李军, 等. 阴阳脏腑体系学说及其临床应用构想[J]. 环球中医药, 2019, 12(8): 116-119.
[14] 朴仁善, 接传红, 王建伟, 等. 从肝脾相关理论论治糖尿病性黄斑水肿[J]. 中医杂志, 2019, 60(5): 78-80.
[15] 徐晓楠, 方钰发, 王妍. 中医阴阳与免疫的关系初探[J]. 四川中医, 2019, 37(2): 25-27.
[16] 陆锦锐, 徐昉, 康利高阁. 中和医派杨建宇教授辨治脉管炎验案赏析[J]. 光明中医, 2014, 14(7): 1508-1509.
[17] 张铁军, 张雪娟, 苗华为, 等. 董燕平教授从相火妄动论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理论探讨[J]. 时珍国医国药, 2017, 16(1): 233-234.
[18] 黄仁发, 林业欣, 高玉, 等. 中医"肺肾交互"理论的探讨及其在急性肾损伤诱导急性肺损伤的物质基础[J]. 辽宁中医杂志, 2019, 46(2): 266-267.
[19] 陈莉媚, 金彤, 宁春桃, 等. 加味四君子汤对H22肝癌小鼠的抑瘤作用和免疫功能的影响[J]. 南方医科大学学报, 2019, 39(2): 121-128.
[20] 赵继荣, 朱换平, 陈祁青, 等. 基于"肾主骨生髓"理论探讨脊髓损伤继发骨质疏松的病机及临床治疗[J]. 中国骨质疏松杂志 2021, 27(1): 131-134,152.
[21] 张艳宾, 曹柏龙, 孙光荣. 国医大师孙光荣教授临证六步法[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16, 14(24): 62-64.
[22] 杨建宇, 范竹雯. 中医万岁!仲圣永辉!——从“经方热”到“经药热”漫谈“经方医学”之中兴[J]. 光明中医, 2018, 33(16): 2436-2437.